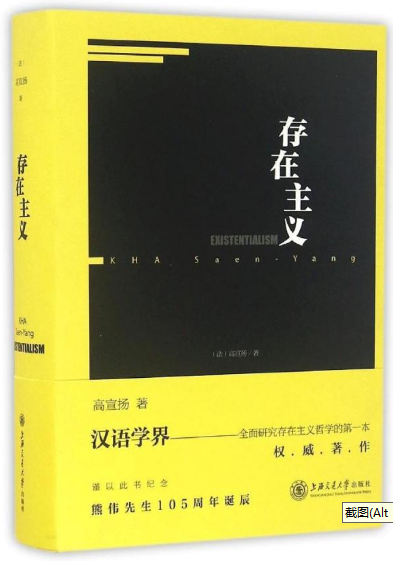从1957年进入北大哲学系聆听熊伟、冯友兰、张岱年等诸多哲学大师的课程,到1979年远渡重洋来到法国第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德里达、福柯、布迪厄、斯特劳斯等20世纪著名法国思想家深入交往,再到2010年成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年近八旬的哲学家高宣扬已经在哲学的世界里流浪了六十年。
这六十年里,高宣扬著作等身。今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了高宣扬文集,最先问世的是《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导引》,之后还将有更多著作陆陆续续出版。
12月17日,一个冬日的下午,高宣扬教授和同济大学中文系的张生教授在上海交大出版社展开了一场对话,主题是“高宣扬哲学流浪六十年”。对于高宣扬来说,哲学不意味着一个学术课题,哲学就是他的人生。

学哲学不但要看懂原文,还要学会原文语言的思考方式
高宣扬受聘于同济时,张生听了两年高老师的法国哲学课。他回忆到高宣扬讲课基本上是直接读法语的,读一段,学生跟着读一段,然后进行解释。
除了法语外,高宣扬还通晓英语、德语等语言。对于高宣扬来说,掌握外语对于学习哲学非常重要,而这样的重要性是他当年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老师们教育他的。
“当时我去郑昕(注:已故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老师家敲门,他第一句话,你会德语吗。我说不会,他说那不行,马上去学德语,到德语专业去上课,不要担心,我马上打电话给冯至,让他教你德语,马上去上。就这样我上了两年冯至先生的德语课。”
高宣扬也提到在北大时,老教授们非常注重看原著。对于一个德语刚入门的人来说,看德文原版《纯粹理性批判》无疑相当困难。“教授跟我说,你要学这个东西必须一句一句来学,很困难怎么办?他叫我每个礼拜用三天的时间,三个下午到他的家去,在他书房里,一句一句地先读先翻译,然后纠正。那段时间,另外有个先生过来了。他们直接讲德语沟通,强迫我听德语。所以踏踏实实地读原著,这是打下基本功必需的,不能逃避的,所以我后来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学会原文语言对于学习哲学如此重要?高宣扬说,“学哲学不但要看懂它的原文,理解它的意义,你要学会用它原汁原味的思考方式,它的语言方式来进行思考和把握它的精神。翻译成中文以后再回过头去研究它的意思的话,因为中文的语言结构和模式不一样,这个模式本身反映了思想精神本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所以要尽可能地——我说的是尽可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尽可能地去学会就它原文、原著反复地读,一次不行,就两次,反复地对它的基本语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理解。”
列维-斯特劳斯每个礼拜花5个小时请教数学家数学问题
张生问高宣扬在法国学习的时候,那些老师是怎么培养研究生,怎么和学生交流的。
高宣扬回忆,他感受到有两个差异。“第一个,法国的教授对研究生是高度开放和自由的,也就是说他把你带进来就让你自由地思考,自己准备论文,自己看书,鼓励你在他们举办的研讨会上去发言,去讨论问题。他们通过你的读书笔记看你对著作的理解达到什么程度。”
第二点是法国老师鼓励学生走出自己的专业框架,进行文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各领域的来往。他特别提到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例子。“他在1930年代,没有正式进入到人类学领域之前,一个礼拜用5个小时的时间去请教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学数学家怎么思考数学,思考高等数学各个方面的成果,来理解人类思考模式的差异性。”
高宣扬也提到“长程迂回”式的学哲学的方法。“后来我接触的另外一个老师,他批评海德格尔在短程迂回。他说我要打破这个短程迂回,从哲学到社会学到人文学到各个领域,再回来到哲学,再从哲学出去,这是一个长程的迂回。他特别强调学哲学的某个专业固然需要专业的研究,但是专业研究不能够离开这些长程的迂回。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育,使我后来也学会除了哲学以外还研究别的东西,这个对我受益很大。”
20世纪法国哲学的发达并非突然,19世纪下半叶就已播种
20世纪是法国哲学的世纪,尤其是1960年代之后,法国突然间涌现了德里达、福柯、列维纳斯、斯特劳斯、利奥塔、鲍德里亚等一大批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
张生援引当代法国哲学家巴丢的说法,提到西方哲学的三个重要时刻。第一个高峰是古希腊,到了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是第二个高峰,第三个高峰就是法国哲学。为什么20世纪的法国哲学如此发达?
高宣扬澄清了一个误解,许多人以为20世纪的法国哲学是突然爆发的,但其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哲学已经开始开出它的奇葩,早就已经打破了19世纪末以前,德国哲学有着重要影响的局面。
“法国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20世纪以后不断创新,主要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的创造精神比较活跃。他们不甘心于停留在原来的西方传统的框架之内,甚至要打破自己的法国传统。19世纪下半叶开始,法国哲学就开始打破笛卡儿的意识哲学。笛卡儿过分强调理性,过分强调历史的作用。从19世纪开始,法国哲学开始向非理性部分——感性部分、感情部分有了新的发展,在这方面法国人应该说比德国人更早一步,因为德国有过这个尝试,在19世纪中叶,先是叔本华,然后是尼采,这两个人都想打破理性主义,但是他们很快被德国的理性主义压下来了。但是在法国,这个东西就一直发展下来。”
因此,高宣扬提醒我们,理解法国哲学在20世纪重要的影响,不要忘记或者说不要脱离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
存在主义还没有过去,精神依然延续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再度打开,西方世界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大陆。在这些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存在主义,手捧一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是那个年代文艺青年的“腔调”。
1978年在香港,高宣扬用三个月时间写出《存在主义概说》,这是汉语学界第一本全面研究存在主义的权威著作,这也是高宣扬第一本引起重大关注的著作。
为什么当时存在主义对19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在回答记者这个问题时,高宣扬首先简单勾勒了西方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它直接与资本主义本身的命运连在一起。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有两次危机,特别是二次大战,对资本主义打击特别严重,那种情况下,西方人开始忧虑,悲观,找不到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存在主义。
同时,存在主义对于自我行动、自我承担的强调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国人。“存在主义特别强调个人走出危机的阴影,靠自己去创造,这是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我先活出来我才有本质,也就是说是我决定我的存在才能造出这个世界。所以萨特在1948年写的一本书里它说什么是存在。存在就是以它自身的显现造就这个世界的存在。什么意思,就是我一出来,我到这个世界上,我要靠我的努力,我的存在造就我喜欢的世界。就是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强调,个人的命运靠自己去决定,自己来创造。萨特讲这句话还特别强调,我强调个人存在,决定自己存在的同时,我特别强调责任的重要性,他说这就意味着当你意识到自己用行动来造就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你必须意识到正是因为这样,你的责任是重大的。所以他把责任的关联和这个存在,创造世界,连在一起。”
这些年,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国内的影响已经远远没有过去那么大了。今天其实已经很少有人再去谈萨特了。对于存在主义已经式微的说法,高宣扬并不完全认同。
高宣扬教授解释道:1980年代到今天,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中国封闭到中国开放到现在发生的时代的改变,同时还出现了一系列的世界性的事件,全球化、恐怖主义、网络化的出现,这些东西使得原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二次大战后流行的存在主义,就显示出它的时代性有点距离了。
但高宣扬认为这个距离是表面的,“存在主义本身的口号是强调个人存在的创造性、自我创造性,创造的同时有责任来改变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精神还是继续延续下来的,而且在现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时代、网络化的时代,越是要显示出个人责任的重要性。”
同时,高宣扬也提到,存在主义从20世纪中叶以后慢慢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法国的新浪潮、新小说都受到存在主义影响,“这说明它的成果不是已经过去了,相反,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去了。”
有机会亲近这么多中外大师,是时代给我的礼物
对于今天的中国学人和普通读者来说,那个大师辈出、星光璀璨的时代已经远去。而高宣扬或许是少数和中外大师有过深入交往的学人。对此,在场的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徐卫翔教授由衷地表达了他的羡慕。高宣扬笑笑说这是时代给他的礼物。
1957年,高宣扬进入北大哲学系时,是北大哲学系大师云集的时代,由于特殊原因,来自全国的哲学教授都调入北大哲学系,当时的北大哲学系集中了35名教授。
这么多年过去,高宣扬依然清晰记得当年在北大课堂听课的场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接聆听很多先生在北大课堂上课的情景。他们讲话的口气、他们对我们的教导,每一段话、每一个概念的解释都是牢牢记在心里。我能够顺利地在1979年以后出国,都是他们给我在心里面种下的种子。”
而说到在法国的三十多年里,他除了感恩还是感恩,“30多年里能和那么多大师交流,我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法国老师对他的意义,除了学养之外,更独特的地方在于,将激情注入到写作和思考中,这是法国思想家如福柯等人的治学行文的重要特点,“他们教我怎么来思考,教我怎么表达语言,教我怎么把情感渗透到文字上面去。情感没有情是死的,生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生命是有感情的。思考也好,写也好,有一种激情在里面,这样的创作和写作是活的。”
张生也说,“以前我们交往的时候,高老师评价一个事物或者强调一个东西特别喜欢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
尽管已年近八旬,高宣扬依然没有停止在哲学王国里的流浪,“我还没有感觉累,脑子里东西特别多,多到感觉很紧张,每一分钟都很紧张,因为要写的东西太多了,要想的东西太多了,要讲的话太多了。”